环境史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热点研究领域,研究历史上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是历史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对推动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包茂红老师界定了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通过解构三个“约定俗成的常识”,总结了环境史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和发展历程。环境史研究在学术上能够创新世界史的编撰,开辟史学研究新前景,在现实中能够为我们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新启示。

一、什么是环境史?
(一)环境史的定义
环境史研究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它部分的历史关系。
环境史中的“人”,不同于还原论和机械论中的“人”。自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以来,人和自然分离,自然“祛魅”成为人类利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条件下,如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自然才会对人类产生反作用。这种作用常被视为偶然事件。环境史从整体论和有机论的视角,重新认识人,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忽略人的自然属性。
环境史中的“人”,也不同于深度生态学中的“人”。深度生态学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忽视了人的社会性。环境史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但不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它绝对化。
因此,环境史中的“人”既是自然和个体的人,也是社会和群体的人。环境史研究这样的人和自然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的关系史。自然作为整体包括三部分,分别是人,与人作用的自然的其它部分,以及未与人作用的自然。当然,未与人作用的部分现在已经很少了。自然的其它部分(the rest of nature)是与人不一样,但与人作用过的自然。自然的这一部分有时也被称为“混杂的自然”。
(二)环境史的研究内容
人为活动引起的环境变迁。研究环境变迁有两条基本路径: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比如从自然角度看,黄河泛滥是由于黄赤交角的变化导致地球气候变化进而引起黄河水量增大造成的;从人为活动角度看,黄河泛滥与农耕向黄河中上游的推进有关。农耕活动引发水土流失,导致黄河水量和淤积发生变化。后者是环境史所要研究的内容。
物质或者经济环境史。主要研究生产、流通、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涉及到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使用科学技术进行加工,到市场中进行交换,消费之后或变成废弃物或变成再生进入经济或者生态系统。
政治环境史。政治是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特定关系。不同利益主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进行博弈,最终形成政治决定和法律。在环境史研究中,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
文化环境史。研究人如何感知环境,这种感知如何指导人们的行动,进而影响人和环境的关系。前现代的人们更多地是在宗教中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同宗教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差异很大。科学革命后,科技深刻影响着人类认识、理解、使用、改造自然的方式。
总之,环境史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有边界。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重点,但都注重研究人与环境在历史上的互动作用。
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现状
(一)解构三个“约定俗成的常识”
常识一:环境史学的兴起是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历史学内部的创新冲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个论点是从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得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反主流文化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平权运动、环境运动等。环境运动的发展要求历史学给出新的解释,这一需求正好与美国历史学自身的“碎化”运动相结合,共同催生了环境史研究。
美国环境史研究兴起的动力机制被美国环境史学家变成了一种普适的路径,并用于分析其它区域和国家环境史研究的而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学术话语霸权的体现,更有意思的是不少非西方环境史学者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体现出“自我东方化”的特点。
如果将目光转向其它地区,就会发现环境史在不同地区的兴起有不同的动力机制和路径。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非洲并没有发生环境主义运动,但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中发生了“环境史转向”。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萌芽的民族主义史学在独立后致力于发现非洲人的历史首创精神,但非洲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均已经被殖民化。经过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后,民族史学家发现真正能反映非洲人历史首创精神的是非洲人很好地处理了自身与地球上最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史学的主题变成了环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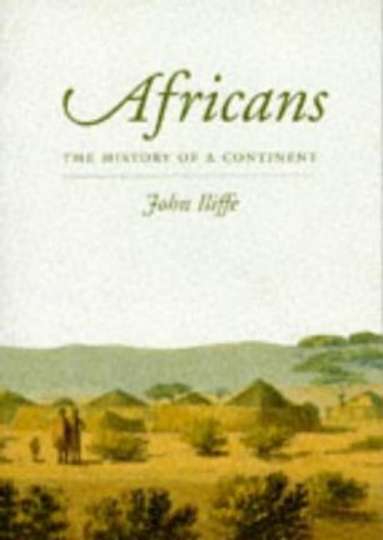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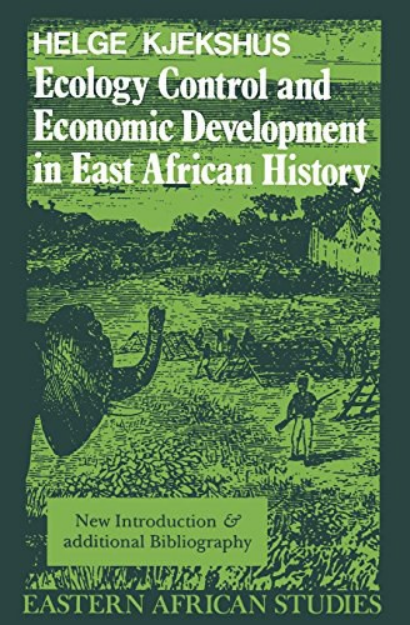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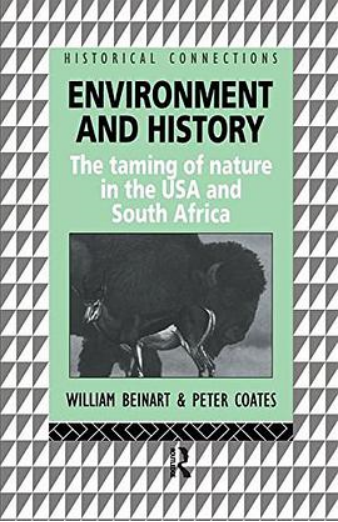
在前苏联,曾经有学者认为环境主义运动和绿党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直到现在,俄罗斯的环境史研究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法国有着把历史学与地理学有机结合的悠久传统,阿拉伯世界也有很好的重视环境的历史学传统,但这两个区域直到现在都没有发展出环境史研究。
因此,从美国环境史研究兴起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其它国家和区域,实际上,环境史学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兴起,都是当地的不同因素凑合在一起、相互作用的结果。
常识二:环境史学从美国兴起后向世界各地传播。
确实,美国环境史学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但这是一种传播主义的观点,其背后隐藏的是欧美中心论。
其实,即使同是工业化国家,各国的研究重点也不尽相同。在地广人稀的美国,环境史研究最初侧重于荒野保护史,欧洲主要研究工业污染史,日本主要研究公害史。即使是研究同一个主题,不同地域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比如在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研究中,美国认为这些地方是无主土地,为了效率、公平和审美需求进行保护。而非洲和印度的同类研究更关注生活在当地的人们的生计。这种研究取向影响了美国环境史研究。卡尔·杰考比就从印度和非洲环境史研究中受到启发,发现美国国家公园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因为先前的研究是以国家公园建立在无主土地的假设为基础的,而这个假设并不是史实,原来这里是印第安人的生产和生活区。对美国国家公园史的解构和重构把美国环境史研究推上了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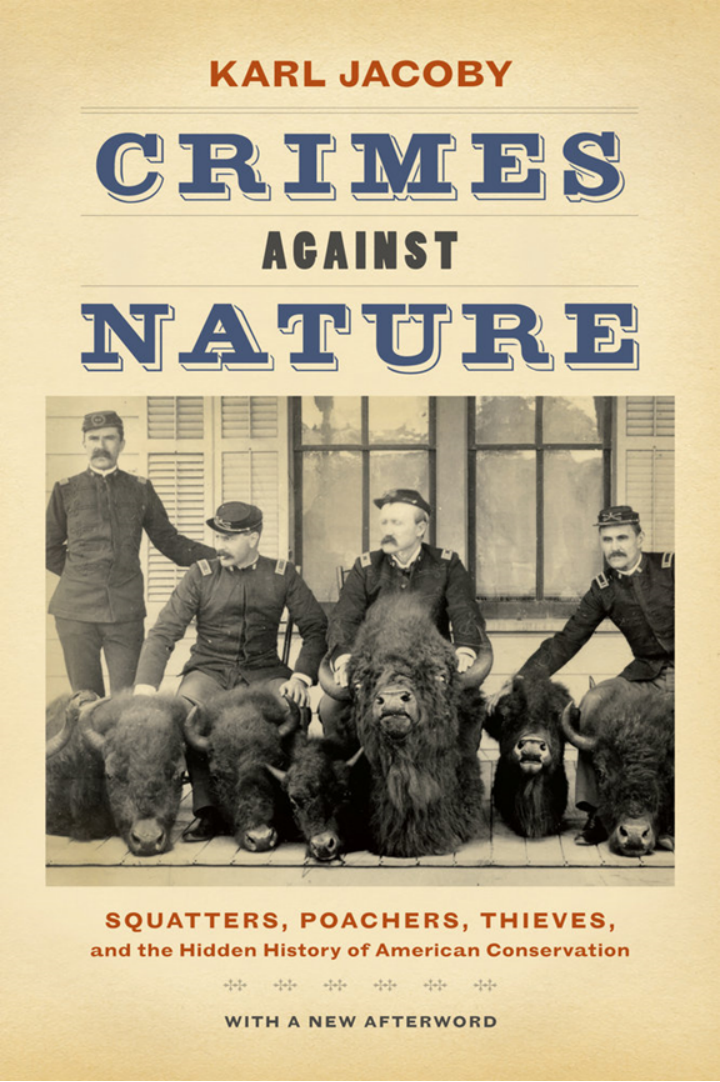
因此,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的环境史研究主题各异,相互交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并非是单向接受或模仿美国模式的结果。
常识三:环境史学起源于18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主要以历史地理学的形式发展。
学术研究中的“爱国主义”是不可取的。对美国的学术霸权不满意,但也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逻辑上看,这种认识与美国部分学者的认识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需要解构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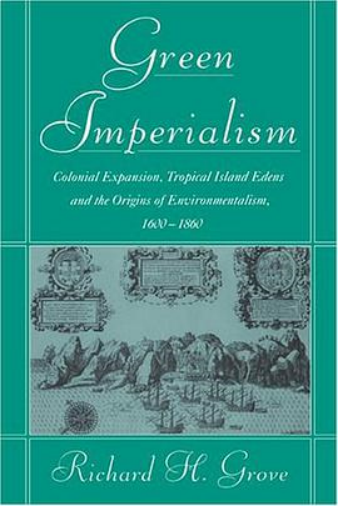
另外,历史地理学不等于环境史。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环境史研究人与自然其它部分的相互关系,历史地理学从剖面重建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地理分布等。历史地理学强调人对环境的作用,反对环境决定论。与此同时,环境对人的作用事实上被忽略。环境史与此不同,强调两者的相互作用。
进而言之,世界各地的环境史研究虽然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但其兴起是时代的产物,这一时代的特点是生态学思维渗透到历史学研究和公众意识。因此,回溯历史不能无限制地向前追根溯源。我们可以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环境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础,但不能说以前的历史地理学就是环境史。
(二)环境史研究的现状
环境史学在部分国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但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环境史已经突破了一些理论难点。先前环境史家争论的一些问题,如physical nature和Human-made nature之分,已基本达成共识。人们的认识已经发展到新阶段,提出hybrid nature or nature as a cultural construction等更符合历史实际的新概念。
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已经确立。采用单一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不能解决环境史研究的主要问题,采用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方法是必须的。
环境史研究的国际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区域研究(Global area studies),从全球的视角研究区域问题。二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zing),全球思考,在地行动。另外,环境史研究也形成了全球化组织,如国际环境史研究机构联盟(ICEHO),它每5年组织一次世界环境史研究大会(WCEH),已经分别在丹麦、葡萄牙、巴西召开了三届。
环境史研究的主流化。主流化有两个面向:一是把原来处在边缘地带的国家纳入核心。在研究英帝国林学知识的生产时发现,核心并不在通常认为的英国或伦敦,而在印度,并经过英帝国的科学网络传到非洲、美国,再从美国传到菲律宾等。
二是对传统史学中的主导性议题进行新的阐释。比如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暴力色彩非常浓烈?环境史研究认为,村庄的公有林地被私有之后,先前以此为生的穷人一无所有,因此暴力革命愈演愈烈。对这类议题的新解释有助于环境史研究进入历史研究的主流。
三、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功能
(一)环境史的主体
传统历史学认为,历史是人有意识创造的结果,在此观念影响下编撰历史是对历史史实和史料的选择性利用。环境史的主体则是相互作用的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它部分。正如William Cronon所言:“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另一位环境史研究的先驱Alfred Crosby说:“人在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资本家或其它什么之前,首先是一个生物体。”换句话说,在环境史学家看来,不仅与人作用的自然具有历史创造力,而且在思考人的历史创造力时也要注意到他作为生物体的一面。
历史学研究也在发生变化,开始重视人的无意识或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直觉引发的,而直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动物性的,不是人所特有的。那么,为什么人的直觉可以创造历史,而动物的直觉就不能创造历史呢?更何况动物还能够制造和使用简单得工具,有自己的情感和社会组织。英国保护生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对黑猩猩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动物世界的奥秘,展示出与人类社会类似的特性。另外一个例子是海狸,它不但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还会筑坝。这个坝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但对海狸来说就是劳动造物。因此,劳动也不仅仅是人的行为,人类面对的自然也不完全是自然的。
植物也与动物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首先,人从树栖动物变成陆栖动物,是森林自身变化导致的。其次,在与人的作用中,森林有自己的演化规律,是自变量。第三,以含羞草为例,它能与人互动,它会影响人的情绪,人的情绪也会引起含羞草的变化。总之,由于环境史主体的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突破传统历史学的概念、范围和原理。
(二)环境史与世界史编撰
环境史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环境史就是单纯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在史学研究中,通常涉及三个方面,分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狭义环境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
广义的环境史是用强调历史的主体发生变化的环境史思维来重构历史。美国历史学会主席John McNeill认为,20世纪历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法国年鉴学派推动的社会科学转向,历史学吸收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方法,构建总体史(Total history)。第二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福柯的影响发生了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历史学采用话语—权力分析的方法,催生了新文化史。科技史研究,尤其是外史研究受此影响很大。第三次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自然科学转向。先前主要依靠文字资料、考古资料、口述资料等都不能完全解决历史难题,需要大量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研究结果,进而结构出与以前的史学大不相同的超级史(Super history)。
(三)中国的世界史编撰
环境在中国的世界史编撰中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过程。
中国的早期世界史编撰有两位代表人物:雷海宗和周谷城。雷海宗在1946年出版《文化形态史论》,借鉴德国的文化形态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这个文化形态史观将文化发展分为产生、生长、衰落和灭绝四个阶段。
雷海宗的观点与黑格尔类似,认为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比如大河流域会形成大河文明。由于受季节影响很大,农耕民族形成了墨守成规的性格,需要君主制。沙漠地带因为缺乏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游牧民族既不受拘束,还要经常骚扰农耕民族,因此这一区域会形成家长制但没有法律。在沿海的希腊,为了征服一望无际的大海,人类需要勇气和力量,进而形成喜好自由的民主政权。
周谷城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历史完形论”,认为世界史是一个完整的形态,不是各个国家历史的拼凑。世界史的演进实际上是在四个系统的演化中完成的,分别是宇宙系统、地球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系统。周谷城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天才的构想,但并没有继续论证。总之,在中国的世界史萌芽时期,学者已经认识到环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继续深入讨论。
20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里完全没有环境的内容。因为这部通史是学习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模式编撰的,而苏联科学院是按照《联共布党史》的模式编撰的,遵循的指导方针是斯大林思想。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自然环境在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苏联经历了五种生产方式,这说明环境没有什么用,更需要重视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世界史编撰发生新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教材中,《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中都有环境的内容和章节。这说明,中国的世界史编撰因应时代变化,重新重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这里的环境史内容只是狭义的环境史。
(四)西方的世界史编撰
西方的世界史编撰可以从三个流派来观察,分别是新世界史、绿化的世界体系史和大历史。
1.新世界史
新世界史有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Felipe Fernandez-Armesto和John McNeill。Felipe Fernandez-Armesto出版了一部影响比较大的教材《世界:一部历史》。在这本书里,他认为世界史由人类史和环境史两部分组成。人类史在整个环境史框架范围里演化,但环境史并不决定人类史,只是为人类史的发展设定了限度。
John McNeill本人就是环境史专家,他结合环境史思维,发明了独特的世界史编撰框架,那就是“人类之网”。人类从自然界演化出来后形成区域性网络,随着生产范围扩大形成第一个世界性网络,而后由于城市革命形成了城市网络,最后形成全球化网络。不同于以文明或国家为基本单位结构历史的基本框架,John McNeill以“五圈层(大气圈、生物圈、表土层、岩石圈、水圈)”为基本单位结构世界史。这种结构融合了历史的断裂性和连续性,融汇了文理两种思维,通过跨学科研究编撰出反映了“阳光下的新事物”的新历史。2006年,我邀请John McNeill访问北京大学,举办了三场学术讲座。2018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客座教授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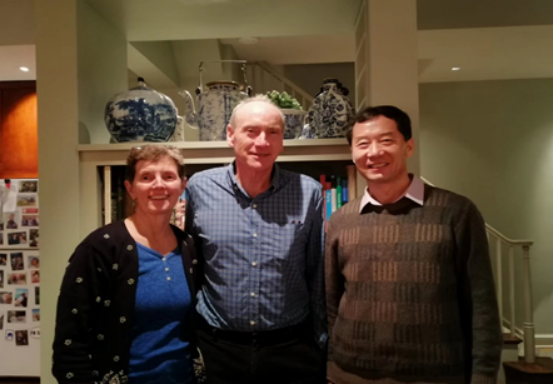
John McNeill教授夫妇和包茂红教授
2.绿化的世界体系史
绿化的世界体系史分两派,分别是500年的世界生态体系史和5000年的绿色世界体系史。500年的世界生态体系史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宾汉姆顿大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Jason Moore教授。大家都知道,世界体系理论是沃勒斯坦在吸收了年鉴学派的方法和理论基础上创立的,但在Jason看来,该理论需要通过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向前发展。他从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概念“oikeios”中引申出新的涵义,进而把50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成了世界生态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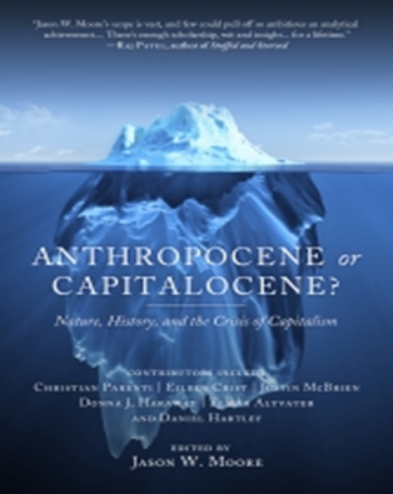
世界生态体形成于14世纪,欧洲在扩张过程中把资源边疆变为商品边疆,促成资本主义产生。因此,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是人类利用自然的结果。到了18世纪,世界生态体发生危机。人们从两个方向化解危机,一是向地下扩张,挖出煤炭带动工业革命;二是向外扩张,在世界各地建立种植园,提供粮食和原料。20世纪80年代,世界体系又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采用“劫贫济富”的方法化解危机。在Jason眼中,华尔街是一种生态组织形式,利用金融重新组织全世界的资源。绿化的世界体系史重新发现了人的自然性。
5000年的世界体系史的倡导者是贡德·弗兰克。他将“资本积累”改成“积累”,从而把世界体系从 500年变成了5000年。贡德·弗兰克还认识到,5000年的世界体系史应该与环境史结合,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概念工具而难以进行研究。不过,贡德的好友、美国华裔学者周新钟顺着这个思路,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出版了绿色世界体系史三部曲,研究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黑暗时代。所谓黑暗时代在环境上的表现就是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它与经济崩溃和社会政治不稳定相互交织,呈现出全方位的危机状态。但这个黑暗时代又孕育着生机,从生态史角度看,由于生产的减少,环境或生态得以恢复。因此,5000年的绿化的世界体系史实际上是生态退化、黑暗时代、生态修复、走出危机等反复出现、周而复始的过程。

3.大历史
大历史最先在澳大利亚出现。一群来自历史系、天文系等不同学科的青年教师合开设一门课程,讲授从宇宙大爆炸直到现在的历史。顺着这个思路,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大历史”流派。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大历史不同于国内流行的、黄仁宇的大历史。如果宇宙历史按比例缩小为13年,那么人类历史只有53分钟,农业社会的历史只有5分钟,工业文明只有6秒钟。大历史给人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我们以前熟知的、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在宇宙历史中是非常短暂和渺小的。换句话说,它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史。
大历史受到比尔.盖茨基金会的重视和青睐。在它的资助下,大历史学家按大历史的理念为美国高中生编写历史教材,希望帮助中学生形成开放性的、大历史的思维,进而在思考世界未来时给人类一个合理的定位。
(五)日本的世界史编撰
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三元结构的文明论,认为日本处在“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元结构中。文明地区是欧洲,野蛮地区是琉球和虾夷。日本本岛处在两者之间的半开化地区,其任务是学习、进入文明地区,同时开化野蛮地区。以此为指导的战前日本发展进程在两颗原子弹轰炸下结束了。战后日本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元结构文明论:文明地区是美国,野蛮地区是共产主义世界,日本处在半文明地区。文明论者对日本重新定位,为国家发展指明方向。
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文明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956年,日本经济指标已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告别了“战后”;1968年,日本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要重新定位自己,文明论者开始摒弃现代化理论,重新从京都学派中寻找有益概念和思路,并通过现地调查和思考形成了 “文明的生态史观”。
梅棹忠夫将欧亚大陆分为两个部分。中部的四大帝国:中华帝国、莫卧儿帝国、阿拉伯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两边的日本列岛和英伦三岛。文明不发达的两边保蕴藏着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在进入近代时平行并进形成了民主世界。环境变化与文明兴衰有对应关系,环境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因此,日本的历史是自主发展而不是模仿的历史,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梅棹的思想被川胜平太继承发展。川胜认为梅棹忠夫遗漏了两个地方,分别是东南亚海域和西北欧地区。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不是从陆上而是从海上兴起的,主要从东南亚海域兴起的,因为在那里形成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商人进行公平交易的自由市场。通过这个市场及其延长线,英国脱离了伊斯兰世界,日本脱离了中华体系,进而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兴起工业革命,通过投资和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日本进行勤勉革命,通过投入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川胜平太提出的文明的海洋史观。
安田喜宪提出了文明的环境史观。他认为现有的世界气候变化图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人类关于世界气侯变化的记录不超过200年,此前主要依靠对来自阿尔卑斯山和格陵兰岛的冰芯测年建构世界气候变化图。安田喜宪认为这个资料来源和构建结果都有问题,因为历史上欧洲人口少,经济不发达,而东亚在历史上曾经很发达,对世界气候的扰动影响最大。如果要建构世界气候地图,来自东亚的史料应该是最重要的。东亚史料从哪里来?一是中国的黄土中蕴含着大量的气候信息,二是沿海湖泊中的年缟。在海洋和大陆的交错地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湖泊,湖底形成一层层的沉积物——年缟。安田通过对年缟测年重建了世界气候地图,但是,由于史料源于日本,这个变化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在气候变化的基础上,从季风亚洲的传统史观、森林民族的循环史观、稻作渔捞民族的和平史观中构建出新史观。
东京大学的世界历史学家羽田正教授倡导把环境史纳入到世界史的编撰。他组建并领导着来自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研究机构的学者组成的“全球史合作研究项目”,进行编撰新型世界史的探索。另外,他还领导着设立在东京大学、跨越传统学科分野、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Tokyo College,对学科走向和世界未来发展进行研究。2019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客座教授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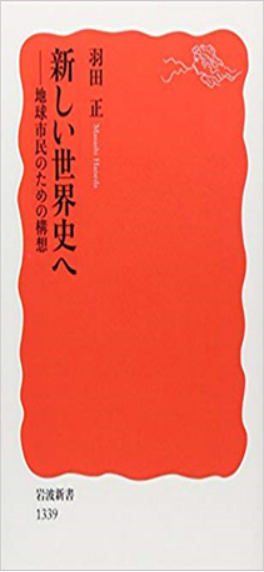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新的世界史观,需要对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定位进行重新认识。那么环境史研究能对建构新世界史观提供什么启发呢?
一,环境史可以帮助从根本上克服世界史编撰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用环境史的思维编撰出来的一定是新的世界史,因为从横向来看,历史的主体变成了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它部分的相互作用,从纵向上看,必须把人类史的演进置于更久远的环境变化中来认识。
二,环境史可以帮助校正进步史观的缺陷。进步史观史单向的线性的进化史观,而环境史思维比较强调环境适应性和持续可能性。根据这一思维,先前被认为是进步的某些历史,可能需要重新认识。
三,环境史有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编撰世界史的瓶颈。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编史容易把世界割裂开,环境史的基本单位有生境、生态区和全球生态系统。如前所讲,John McNeill试图用五圈层框架结构世界史,这与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三圈层框架(自然圈、人间圈和生命圈)不谋而合。据此编撰的世界史显然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传统的世界史。
四,环境史可以帮助世界史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环境变迁的规律统一起来。由于学科分野,人文社科研究中探寻的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科学探寻的自然规律基本上是平行的,没有交集,环境史可以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而把两类规律统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能量流动和规模扩大。
四、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不同,历史学并不擅长预测或提出对策,但历史学能够提供启示,学史使人明智。在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时,运用环境史思维可能能够获得一些独特的认识。
其一,以生境多样性为基础,文明多样性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建立在进步观念基础上的线性历史观需要修正。以此来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现多元可持续的未来(sustainable futures)可能是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愿景。
其二,从人与环境是个整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必须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任何发展项目在立项实施之前都必须做环境影响评估和战略影响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各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参与必不可少,尽管谁能代表环境和后代的难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因此,人类在发展时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因为人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
其三,世界环境史昭示,现在处于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和国家有可能后来居上,但后来居上者要维持不那么容易,需要具有普适性的“软实力”,其中人与环境关系上的新认识至关重要。
其四,从环境史整体论和有机论思维出发,认识到每个人至少都有两个祖国(民族国家和地球)和两种终极关怀和责任(人类和地球命运)。在此基础上协调民族国家公民、区域住民和地球村村民、发展中国家、发展组织与工业化国家、民族国家、区域组织与国际社会,私有权与Commons等关系。
纪要整理:贾雨心
配图:贾雨心张雪梅
编辑/摄影:张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