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当代史:我们当下的境遇
如今我们正在一场疾疫的大流行中。2020年2月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将不明原因的肺炎暂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2020年2月11日 WHO将其命名为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2020年3月11日 WHO宣布疫情可以被称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这使得对于pandemic开始和结束的判定权掌握在WHO的手中。2022年9月14日WHO宣布:“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但终点就在眼前!”(We are not there yet. But the end is in sight!)疫情似乎快结束了,但是2022年9月22日WHO又宣布:“我们还在隧道里!”( We‘re still in the tunnel!)这意味着,全球大流行似乎还没有结束甚至即将迎来第四年。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境遇,也是最切近的当代史。当历史的进程在我们身边流动,我们被过量的信息所包围,却又遭遇着复杂而破碎的信息。于是,历史学家总会问:我们记得什么?如何记得?我们当下应该还记得口罩、核酸、健康码、疫苗和隔离,但是在疫情之初一些曾被反复提及的故事,与动物有关的故事,却似乎已经被遗忘。而这次课程希望重访这些故事。
02 病毒溯源与动物的故事
随着疫情的爆发和传播,越来越多的动物被认为是源头或与这种疾病的可能联系如蝙蝠、果子狸、穿山甲等,尤其是蝙蝠。马修·博尔加雷尔(Mathieu Bourgarel),是法国研究机构农业研究发展中心(Cirad)的病毒猎手,他带着口罩、穿上防护服带上手套,全副武装后潜入蝙蝠洞穴,采集蝙蝠的样本和粪便带到实验室,对蝙蝠携带的各种病毒基因物质进行抽样和排序。他们已经发现了不同种类的冠状病毒,包括一种与“非典”(SARS)和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同属一类别的冠状病毒。调查蝙蝠所携带病毒的多样性和基因组成,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提供快速应对工具是世界性行动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病原体顾问、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过去10年一直在行动,他和它的团队访问了20多个国家,试图通过在蝙蝠洞穴中寻找病毒、预测大流行病,他们在2013年的云南蝙蝠洞找到的冠状病毒样本与新冠病毒最相近,至少有96.2%的相似度。中国研究蝙蝠的专家罗波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蝙蝠与新冠病毒关联被证明之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都出现“恐蝠症”

Mathieu Bourgarel

罗波正在开展中国蝙蝠调查与保护,他搜集八十二国、上千名蝙蝠研究者的意见,当中并无一人,因研究或观察蝙蝠而染疫。对蝙蝠和其它野生动物的迫害有可能使公共卫生状况恶化,而不是改善,因为砍伐森林、集约化农业和野生动物贸易等活动都增加了疾病从野生动物向人类蔓延的风险。病原体要发生跨种感染,必须克服一系列的生态屏障,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自然世界,那些帮助抵抗传染病蔓延的屏障就会被打破。

在疫情期间人们将罪责推给蝙蝠等野生动物时,动物们的生存如何呢?2020年5月5日,泰国国家公园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组宽吻海豚照片。自泰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部沿海各府相继关闭海滩,暂停非必要的海上活动,游客锐减,海洋生态环境得以恢复,海洋动物自由出没。同时期在意大利封锁期间人们也看到了海豚和天鹅在威尼斯游泳。动物们似乎迎来了他们的动物乌托邦(Zoo-topia)。在这些叙述背后呈现出两种假设的冲突:来自野生动物的疾病是人类健康的威胁?还是人的活动是野生动物的威胁?

动物和病毒的故事还在延续。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疫情之初的相关新闻,2020年3月4日,香港渔护署确认新冠感染者家中的宠物狗核酸阳性,2020年3月16日,香港感染新冠的宠物狗死亡(不确定是否是新冠导致的);2020年4月23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Bronx Zoo)内又有7只大型猫科动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包括4只老虎和3只非洲狮;2020年4月荷兰农业部宣布有雪貂农场的貂被感染新冠,大概率是被感染新冠的工人传染。这些社会新闻在告诉我们,在证实人类被动物感染之前,人类也感染了其他动物。
03 恐惧的历史叙事:疾疫全球大流行的世纪与动物的复仇
过去的一个世纪,被有的医学史研究者称为疾疫全球大流行的世纪(The Pandemic Century),在这个疾病流行的名单中,包括艾滋病、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禽流感、塞卡、埃博拉、拉沙热、尼帕等,新兴病毒不断被发现与证明,人类的疾病谱也在爆炸式地更新,其中人畜共患病占新发传染病的大多数,如1976年埃博拉出血热、1996年的疯牛病等。人畜共患病是由某种病原体从动物溢出传染给人类而导致的,动物被当作病媒、人和动物的共生病等观念的结合指向“动物可能引起下一次的疾疫”。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专设一章题为“牲畜的致命礼物:病菌的演化”,其中用全球机制解释了这一点:欧亚大陆逐渐发展出的牲畜驯化,驯化的牲畜后群居使得疾病流行,群居牲畜的流行疾病会传染给与牲畜密切接触的人类,牲畜的流行疾病成为欧亚人群的基础疾病后,随着欧亚人群的流动传播到新世界。
1997年香港首次发现H5N1病毒个案,几年后,H5N1病毒在东南亚传播、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大流行的担忧,当H5NI病毒从亚洲传播到欧洲时人们担心它可能引发一场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在禽流感大流行恐慌最严重的时候,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出版了《怪兽在我们家门口:禽流感的全球威胁》(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戴维斯认为这种疾病在亚洲的出现是由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南方是家禽的驯养地,这种动物在工业化养殖中具有高产肉量的潜力,禽鸟向人类传播流感被认为是动物对饲养环境和人类的报复,动物在感染人类的时候回到野生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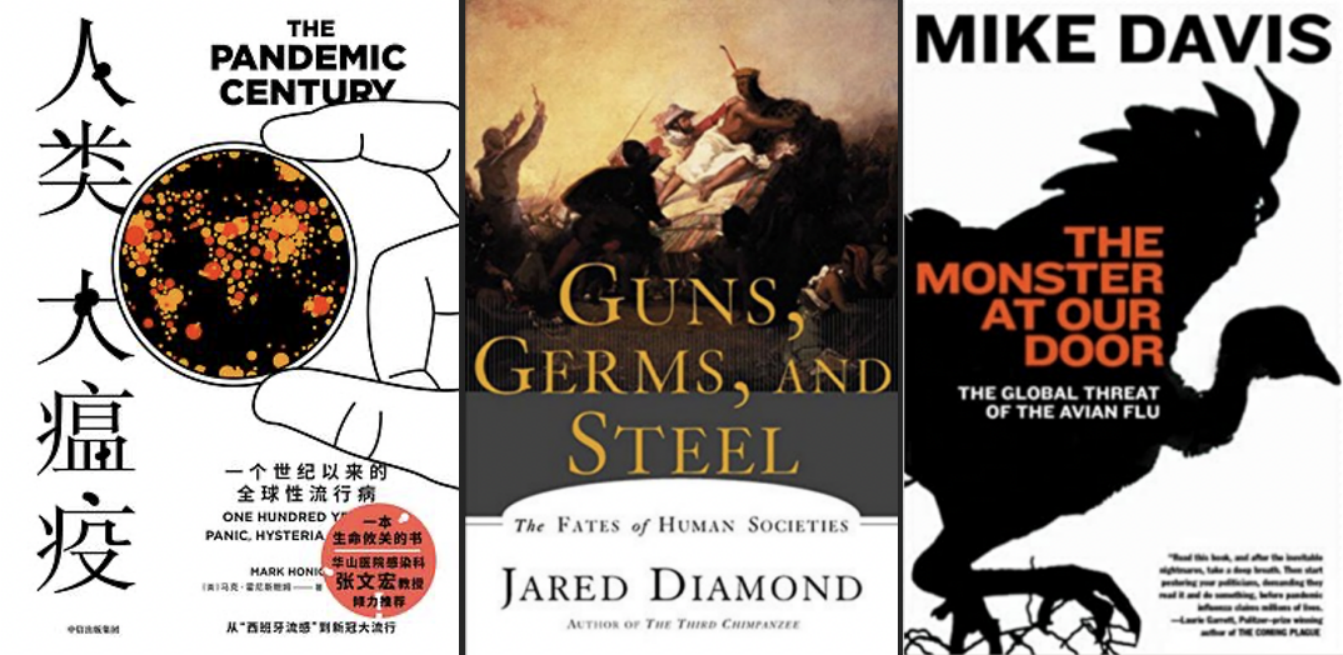
蚊子是也常见的“反派”之一。人类使出浑身解数对抗蚊子,目前所知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除了疟疾还有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黄热病、黑热病、丝虫病。微软(Microsoft)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2018年世界蚊子日(World Mosquito Day)表示“我讨厌蚊子。他们传播的疾病每年夺去50多万狮子的生命。事实上,蚊子一天杀死的人比鲨鱼100年杀死的人多!”通过这样的比较,蚊子被渲染为一个可怕的对象,被塑造为一个“掠食性”物种,蚊子是如何在公共领域被塑造为流行病恶棍的?蚊子会杀人吗?还是蚊子在无意中传播了传染病的病毒?

这样的论述有其历史渊源,蚊子病媒论以及疟疾生态学是在19-20世纪殖民地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罗纳德·罗斯 (Sir Ronald Ross)出生在印度,随后前往伦敦圣巴塞洛医学院学医,1881年前往印度军队医疗服务,1892年开始研究疟疾,当时疟疾在是个各国流行,罗斯随机组织预防疟疾运动,当时有人认为是沼泽地里的不良空气导致疟疾,罗森怀疑疟疾与蚊子的关系,蚊子在水中繁殖,他开始注意蚊子繁殖地与疟疾的关系,随后在蚊子胃肠内发现了疟原虫,证明了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190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爵士(Sir Arthur George Tansley)明确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整个系统(从物理学中的意义来说),包括了有机体的复杂组成,以及我们称之为环境的物理要素的复杂组成,以这些复杂组成共同形成一个物理的系统。……我们可以称其为生态系统。”而所谓“疟疾的生态学”也试图建立一个以病媒为中心的复杂系统,但是其目的在于防控疾病,了解病媒的生存环境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病媒,阻断疾病的传播,疾病的生态学也就成为驱逐恶棍的武器。对于蚊子与疾病的了解,在美国陆军军医威廉·克劳福德·戈格斯 (William Crawford Gorgas)手中成为了应对黄热病的工具,当时尚不确定黄热病的病原体,但是确定此病与蚊子叮咬有关,军队开展灭蚊运动,将所有黄热病患者隔离在防蚊纱窗后,化学药品熏蒸、掩埋蚊虫滋生地,杀死蚊子及其幼虫,以控制黄热病。
这样的灭蚊/根除疾病运动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20世纪初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成立了专注于医药卫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01年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13年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负责国外卫生工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基金会的公共卫生活动坚信:“疾病是人类生活的终极弊病,而且还是其他所有弊病——贫穷、犯罪、无知、恶习、无能、世代相传的污名和许多别的罪恶——的主要来源。”因果关系不是贫穷导致疾病,而是疾病导致贫穷,根除疾病就可以铲除阻碍经济生产的障碍以及列举的所有弊病。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事业影响重大,到1951年其国际卫生部终止工作时,它的工作人员在全球80个国家从事过公共卫生工作,因此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干预为导向的工作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之后里主导了国际公共卫生活动。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公共卫生方面最初是解决钩虫病问题,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末结束了钩虫病项目,随后将资源转移到黄热病与疟疾的根除行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疟疾根除行动,控制蚊子和幼虫从而控制疟疾最终根除疾病。新的英雄随之登场,弗雷德·洛·索珀 (Frederick Lowe Soper) 担任全球疟疾根除计划负责人,索珀表示:“(刚到南美时),我当时连一只蚊子也没杀死过。”但随后他却成为了蚊子杀手(The Mosquito Killer),因为他坚信:“追捕每只蚊子,要比追踪每个患者容易。”
Frederick Lowe Soper
(1893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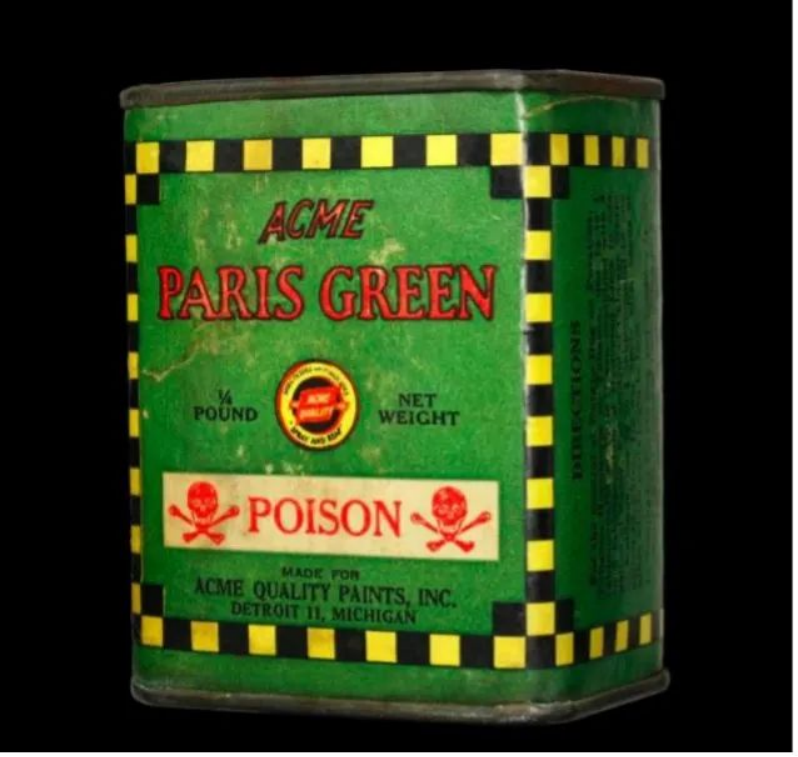

杀死蚊虫的化学药品在更新换代,20世纪前是生石灰,20世纪初是石蜡原油混合剂,20世纪20年代是“巴黎绿”(paris green),20世纪30年代是除虫菊酯,二战后的DDT成为新型杀虫剂宠儿。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严厉批评了DDT使用狂热所带来的环境危害:“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由于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更高级进化从而获得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兹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品,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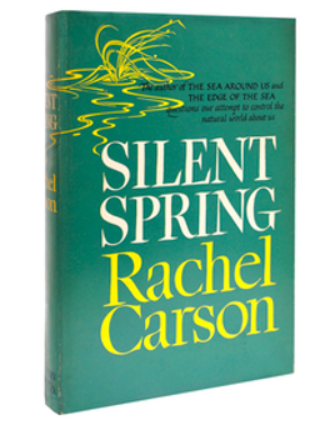
Rachel Carson (1907-1964)
由此,另一种疾病生态学诞生,医学(即根除疾病)视野下的疾病生态与生态视野下的疾病生态,前者以人类为中心,旨在塑造只有人类的生态乌托邦,而新的生态学则要求我们承认,人与非人都存在于生态网络之中,渴望人类与其他生态的生态乌托邦,而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é Jules Dubos)已清楚的宣布了基于旧的疾病生态学的疾病根除计划应该被终结:“疾病根除计划最终会变成图书馆书架上的古董,就像所有社会乌托邦学说一样。”但是人类还是执着于杀死蚊子以根除疾病,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灭蚊也有了新的方向。2018年比尔·盖茨将投入400万美元用于英国Oxitec公司转基因蚊子计划,该项目旨在培育转基因雄蚊子,通过交配杀死雌蚊,这种转基因雄蚊体内携带一种特殊蛋白,该蛋白会导致它们与雌蚊交配所产生的雌性后代在成熟咬人之前就死亡,减少雌性蚊子的数量,从而降低疟疾在人类的传播。
是否存在“疯狂计划”之外的常规应对方式?或许动物不是“病毒储存库”(virus reservoir),而是与人类一起做“准备”(preparedness)的哨兵。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以病原体跨越物种间障碍为出发点,探索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关系的转变。他重点讨论了,我们是否可以从鸟类本身的角度来理解病原体,以及在动物层面对新发传染病实施防范措施意味着什么,凯克将策略分为三类:遏制(prevention)、预防(precaution)和准备(preparedness)。遏制是根据对社会的风险,特别是在面对霍乱、结核病、天花等传染病时,对某一特定领土内流行病传播风险的估计。预防原则是最大限度地估计风险,因此国家应全面参与,特别是大规模扑杀疑似感染的动物,例如在疯牛病和禽流感的情况下扑杀(culling)牛和鸡。准备需要及时监测和控制可能出现在世界任何角落的潜在大流行病毒的传播,如野生鸟类禽流感的监控与家禽哨兵的设置(如健康并且未注射疫苗的鸡被当作“哨兵鸡”放置入养殖场,以此检测其他鸡群是否携带病毒,发现可能出现的传染病以做好准备。)准备工作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因此防范工作不再由国家组织,而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来组织。凯克强调准备是应对跨物种疫情的最佳策略,他表示近年来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巨大变化,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和家养动物数量增加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这增加了病毒跨物种传播的机会。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与动物的关系,学会通过动物的眼睛来理解病毒以防控传染病。

04 余语
这也许是一个应该向刚离开我们的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致敬的时刻!正如他所论证的那样,微生物学可被视为一种将社会重新配置为人、动物和微生物之间的关系链的方法,在这种关系链中,动物表现为微生物的携带者,动物因其携带的病原微生物变成人类文明的敌人。根除疾病的幻觉,是企图通过杀死动物携带者的简单动作将疾病的存在抹去,因此在抗击流行病的戏剧中,病毒猎人和病毒携带者成为敌对的双方,动物往往被塑造为“恶棍”,承担罪责,这样的描述实际上过分简化了导致传染病大流行的生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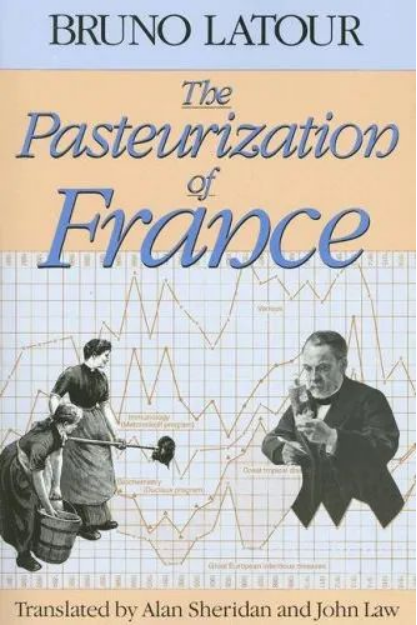
现实是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非人类动物,我们都共存一个生态圈,而且随着气候和土地利用的变化将进一步促进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外溢。科林·卡尔森(Colin Carlson)及其团队利用哺乳动物-病毒网络的亲缘地理模型模拟了未来病毒共享的潜在热点,并对2070年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情景下3,139种哺乳动物的地理范围变化进行了预测,在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亚洲和非洲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相关病毒的跨种传播估计达到4,000倍。这种生态转型可能已经开始,在21世纪将升温控制在2°C以内不会减少未来的病毒共享,卡尔森和他的团队的研究成了一个糟糕的预言,意味着当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并不能减缓人畜共患病的外溢,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如何想象自己与地球的未来,我们要与谁一起生活在生态系统当中。在这时,也许新的科学能提供新的方案,但是重思我们与动物的历史,特别是在恶劣的状况,比如疾病大流行时,我们与动物的历史,显得也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历史在塑造我们要与谁一起生活在生态系统中的想象。
文字整理:蓝贻茜
排版:胡潇月
编辑:张雪梅

